这世界是一个整体,现在大家都在不断地瓦解、粉碎它。也就是说,整体性观念早已不合时宜,被称为假相,每一个人都在喊:“告诉你吧,世界,我——不——相——信。”但我们这样喊的时候,可能没有意识到又一个整体的形成。
所以,当我想用“被拆解的整体”作标题时,我发现诗人冷眼在此问题上心怀鬼胎。比如,有时他说,整体可以被拆解;有时他问,被拆解的整体还是不是整体;有时他又相信,人生来就被赋予整体的观念,在整体不存在的时候,他会自动生成一个令他满意的整体。第一个冷眼与我们所见的以解构为乐的庸常者没有太大区别,他们自称先锋;第二个冷眼令人尊敬;第三个冷眼是真诗人,因为他洞察了人的生存的某些奥秘。我这样说不免把一个好端端的诗人分裂成了几个,但其实这正是诗人冷眼惯用的手段:整体在其诗中被表述为一个,另一个,又一个,再一个……却仍然从属于特定的那一个。
也许第一个冷眼并不存在,因为他对拆解之物的态度令人有些捉摸不定。《齿轮吻合》中,“我们”当然是为了吻合的目的而被分别制造、装配的,无论过程怎样复杂都是为了咬合一体。但当“我们”不断撞见“一对相互修补断牙的齿轮”时,情形突然变得微妙:“我们”的过去就是他们的过去,“我们”的将来也就是他们的现在。更要命的是,加诸两者“不断撞见”之间的情绪的交流状态,被有意模糊,诗人的情感倾向十分含混,难以言表,这从“匀速,静止”的悖论中凸显出来。易言之,脱离了“我们”这个整体的那对齿轮依旧是一个整体,唇齿相依,但是,如何才能将快乐与悲伤、幸运与不幸、奴役与自由这些东西合理地分配给“我们”与“他们”?在持续不断的看与被看之中纠结的,是一团乱麻。
第二个冷眼倾向于认为,整体不是假相,以为整体可以经由拆解而消灭才是一种天真的假相,就像群猴在水中看到的月只是月的影子。说直接一点,诗人认为整体的事物具有循环的功能:整体——拆解——还原。这种循环功能可用《齿轮吻合》中的“来回运转”概括。在《一声诅咒》中,“灵魂的软蛋”“从身体里出发,又转回到我身上”,是粗野的驱逐对象;但没有它粗野根本无从现身。《鬼胎分娩》中的亡灵是另一个“我”,而这一个“我”也不过是词语的亡灵。父亲的零件在重新组装、加油、打磨之后将再展雄风,冷酷的词语下有着抑制不住的亢奋。我不知道还有谁像拆解、离析机器一样解剖、观看父亲的五脏六腑,却又毫不掩饰自己希望复活一具整体生命的强烈幻觉。《没有终止》中,死亡已在另一个生命中潜伏下来,获得新生。《作为幻觉的想象》则直截了当地表达了需要另一个“你”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,他既忠实又叛逆,有离去必有返回。
当确认只有一个声音的时候,还可不可以使用“交谈”一词?第三个冷眼说,可以:
……始终只有一个声音
隔着走廊和走廊上银灰色的灯
隔着我跟我的父亲
查房后离开的护士
以及床单下熟睡的那些接二连三的病历
低声交谈:“进了医院
我就更像一个病人。”
这由整体分娩出的鬼魂,着实让不信鬼魂的我吓了一跳。我来回阅读这首诗,确信是医院那无处不在的诡秘氛围在捣鬼:它先于我们而存在,驱使我们将分隔的、不相干的事物捏合一团,以窥探新的秘密。这里,医院影射着社会的总体性构成,人与人之间一道又一道的“隔”,其实是通往“不隔”的条条走廊。在这里,看似不同的人共有着同一个身份,秘密是为了公开而紧张、持久地蓄谋着。
这个冷眼很像一位结构主义诗人,一位在解构的狂欢中寡言少语的人。他的冷静、克制的语调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。理想的状态或许是按他的方式,把三个人捣碎再捏一个,不那么冷静、克制而又执著于一与多的循环往复。因此,我同样偏爱《吃我的粮,骂我的娘》中那股“反骨头”的酣畅淋漓的激情:
他是那么容易愤怒,他是那么容易
像一个纯正的禽兽吃饱了食物
披散着松软的皮毛,躺在松软的土地上
在太阳下晒暖,并不打算马上离开;
他在这块土地上,在他划分的省份中
吃饱喝足了,并用这里的泥土
为自己捏出一对儿女,那受孕自
另一个女人肚子里的外省之省,我的;
他吃饱喝足了,这个禽兽
他开始糟蹋这块松软的土地
给他提供的欢娱,沉醉,花粉和麦种;
他开始运用他的象征,他的笔法,题目
他的保皇党的父亲的手枪
他的心里的贱骨头,他的反骨
永远都不会满足,永远都不会满足;
诚然,他得把自己包裹得像一个纯正的禽兽
每天出门都不会脱手扶正
他的深绿色的眼镜,这里,那里,高声叫着
瞧呀,又是这个省份里的人众。他的贱骨头,他的反骨。
2004年2月
汉口真无观
原载《文学教育》2016年第9期上旬刊
插图来自网络
冷眼的诗
齿轮吻合
说说过去,说说过去吧,
我们,这两个齿轮,
分别在两个加工厂,
分别被两个汽锤锻造成型,
分别在两张车床上,打磨,抛光
又分别进入流水线磨合期试验的绞盘;
之后,我们分别被装进同一个机舱
组成配件,一个整体;
在润滑剂,防腐剂
离合器跟加速度的反复作用下
来回运转;其间
我们不断撞见
一对相互修补断牙的齿轮
在我们下方,匀速,静止。
隔着走廊和门
一个很深的夜
医院的走廊上,我听到
有个声音低声在跟谁交谈;
起初,我以为,那是两个熟人
之间,避开别人的谈话;
是一个病号跟一个陪护
一个病号跟一个病号
一个陪护跟另一个陪护
他们在交谈,有关病情或者别的什么事故;
可是后来,我发现这些都不是,
不是,因为始终只有一个声音
隔着走廊和走廊上银灰色的灯
隔着我跟我的父亲
查房后离开的护士
以及床单下熟睡的那些接二连三的病历
低声交谈:“进了医院
我就更像一个病人。
一声诅咒
从身体里出发,又转回到我身上。
乒乓球在球桌上滚动
因为是圆的,没有球拍
因为在盒子里,没有网,无法碰撞和传递
这白色的,像是灵魂下的一个软蛋;
现在它跑回来了,钻进我的袖口
占据我的起居室,牙膏,水果,拼盘
占据我的可视屏幕,暗红色的实木家具
一套酒杯;又乒乓两声
从我的脚下滚走;滚吧,滚远一点。
父亲打过吊针之后
葡萄糖和盐。冰凉的水。
他体内的马达将要轰鸣
并注满了油,准备转动;
另外还有,随着他体内的马达
将要一起运动的
他体内的电工刀,起子,扳手
一卷防水胶布和吊机;但他的配电盘
却已老化,落伍,不能起到
继电保护作用;别的配件也急需重组
装成系列配套供应的并联机组
电表,电容,闸刀,钢丝绳,畅通的线路;
现在,一块止血胶布
在他的左手背上
正沿着打开的豁口
向他体内运送
成吨的黄油,三角带和翻砂过后崭新的喷头。
作为幻觉的想象
你要找到这样一个人:
他能安静地听你倾诉,在你的眼神中
他能看到他所熟悉的那个世界,
你们两个人的世界;
在这个世界中
有暴力和软弱,湖水和冰,
有枝头的麻雀,盘曲草丛中的蛇,羚羊
老虎,蜥蜴也伸出了头,在探望;
这些他都能看到,都能静心聆听,
朝向你挪动他的身体,伸出他的双臂
紧紧抓住你的后心,而后拂袖而去,
像一个房客,乒乓甩响你追加房租后的房门;
但你始终都会相信,不久他会返回。
诗的诞生
再没有什么可输。
在那间宽大的地下室。
再没有什么可输。
在那赌红了眼的赌徒当中。
在那伸进口袋里的手再也掏不出什么。
在那对以往无边的仇恨和反悔中他写下这第六行诗。
真无观:与他者比邻而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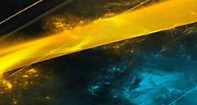


评论列表